内容简介 · · · · · ·
一位67位岁的中国画家,支起画架,安顿好三脚凳,安然从在巴黎塞纳河畔、翡冷翠(今通行译作佛罗伦萨)优雅的街头,专心画他的画。这是1991年的春天夏天的事情,画家黄永玉完成了他两次丰盛的艺术的旅程。黄永玉是一位杰出的画家,其写的散文等文学作品都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为其在国外小住时所写的艺术游记散文集,由三联书店在1999年《黄永玉艺术展》前精心制作出版。每篇文章都配有黄永玉先生所作的油画、水彩等总计数十幅为本书增添了不少色彩。读这两辑游记,我们如同与画家一起,沿着塞纳河,踏着当年印象派画家的脚步,来到处处入画的梵高故乡,又与画家一起,崇敬地来到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生活的地方,呼吸着那仍然留下来的醉人空气。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创作者
· · · · · ·
-
 黄永玉 作者
黄永玉 作者
作者简介 · · · · · ·
黄永玉 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一九二四年出生,受过小学和不完整的初级中学教育。做过瓷场工人,小学、中学教员,报社编辑和记者,自由撰稿人,电影编剧、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自学美术、文学、长期从事版画、国画、油画、雕塑、漫画创作;此外还写过不少散文、杂文和诗歌,也创作过剧本,有很高的文学造诣。
目录 · · · · · ·
沿着塞纳河
沿着塞纳河
是画家的摇篮还是蜜罐
追索印象派之源
“老子是巴黎铁塔”
飞来与我们喝早茶的金丝雀
忆雕塑家郑可
“可以原谅,不能忘记!”
洛东达咖啡馆的客人
让人记挂的地方――洛东达咖啡馆
梵高的故乡
巴黎――桥的遐思
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
翡冷翠情怀
意大利的日子
每天的日子
也谈意大利人
菲埃索里山
高高的圣方济哥修院
咸湿古和薄伽丘
纪念馆和薄伽丘
大师呀!大师
我的意大利朋友
没有娘的巨匠
杜鹃随我到天涯
教训的回顾
皮耶托、路易奇兄弟
了不起的父亲和儿子
但丁和圣三一样
牧童呀!牧童
司都第奥巷仔
婀婀河上的美丽项链
迷信和艺术的瓜葛
大浪淘沙
爱情传说
罗马,最初的黄昏
什么叫公园
好笑和不好笑
圣契米里亚诺
米兰与霍大侠
离梦踯躅――悼念风眠先生
西雅娜幻想曲
永远的窗口
后记
· · · · · · (收起)
沿着塞纳河
是画家的摇篮还是蜜罐
追索印象派之源
“老子是巴黎铁塔”
飞来与我们喝早茶的金丝雀
忆雕塑家郑可
“可以原谅,不能忘记!”
洛东达咖啡馆的客人
让人记挂的地方――洛东达咖啡馆
梵高的故乡
巴黎――桥的遐思
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
翡冷翠情怀
意大利的日子
每天的日子
也谈意大利人
菲埃索里山
高高的圣方济哥修院
咸湿古和薄伽丘
纪念馆和薄伽丘
大师呀!大师
我的意大利朋友
没有娘的巨匠
杜鹃随我到天涯
教训的回顾
皮耶托、路易奇兄弟
了不起的父亲和儿子
但丁和圣三一样
牧童呀!牧童
司都第奥巷仔
婀婀河上的美丽项链
迷信和艺术的瓜葛
大浪淘沙
爱情传说
罗马,最初的黄昏
什么叫公园
好笑和不好笑
圣契米里亚诺
米兰与霍大侠
离梦踯躅――悼念风眠先生
西雅娜幻想曲
永远的窗口
后记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
“我这个老头丝毫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知识,却也活得十分自在快活。 我要这些知识干什么?极系统、极饱和的庞大的知识积聚在一个人的身上, 就好像用一两千万元买了一只手表。主要是看时间,两三百元或七八十元的 电子表已经够准确了。不!意思好像不是在时间之上。于是,一两千万元的 手表每天跟主人在一起,只是偶然博他一瞥。 “读那么多书,其中的知识只博得偶然一瞥,这就太浪费了!“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读 书。 “认认真真地做一种事业,然后凭自己的兴趣读世上一切有趣的书。 “世界上的书只有有趣和没有趣两种。有益和有害的论调是靠不住的。 这个时候有益,换个时候又变成有害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页 -
桥是巴黎的发簪。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4页
> 全部原文摘录
喜欢读"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人也喜欢的电子书 · · · · · ·
支持 Web、iPhone、iPad、Android 阅读器
喜欢读"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人也喜欢 · · · · · ·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书评 · · · · · · ( 全部 123 条 )
承袭黄老头一如既往的温暖的集子
一般来说,温暖是我对人或物最高的评价。既包含对有此种品性的人物的欣赏,也包含从心里生出的不自觉的喜爱。 作家出版社这几年出了不少精致的书,董桥那几本就做得和Oxford版一样古典。素色的硬皮封面,烫金的边纹和字。不管是抄袭还是借鉴,亦或只是作者本人的要求,至少看...
(展开)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比我老的老头》火得腾~腾~腾,知道了黄永玉是沈从文表亲。 黄苗子也火了,嚯~嚯~嚯,知道了黄永玉是黄苗子的铁哥们。 《一路唱回故乡》仿佛这火的苗头,灼~灼~灼跳跃着,就算被畅销烫一下也无妨,站在书店里,先翻翻。 兴高采烈的天真,书名透出的气息扑面而来。先入为主也是...
(展开)
《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 設計手記——跟著黃永玉去遙遠的藝術國度遨遊
黃永玉先生在中國當代美術界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很幸運能夠設計黃永玉大師這本《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的繁體版書籍。 拜讀文稿的過程中看到黃永玉大師用清晰、明快、美妙的語言敘說着他在巴黎和翡冷翠期間,有趣的所見所聞,還有北京等地的一些故人和往事,字裡行間透露着對家...
(展开)
论坛 · · · · · ·
| 这不是那个有名的老头子么! | 来自Vincent豆瓣酱 | 2009-12-24 18:59:14 |
这本书的其他版本 · · · · · · ( 全部7 )
-
作家出版社 (2006)8.7分 7749人读过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8.7分 1125人读过
-
作家出版社 (2023)9.2分 471人读过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8.6分 283人读过
在哪儿借这本书 · · · · · ·
以下书单推荐 · · · · · · ( 全部 )
- 黄永玉 (davidguo)
- 笑嘻嘻读完的书 (aloneiris)
- 藏书阁三十二大 (藏书阁)
- 我的电子书1,待待待待待续 (|SLW~)
- 爱智慧,从悦读开始(09书读书总结) (aloneiris)
谁读这本书? · · · · · ·
二手市场
· · · · · ·
订阅关于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评论:
feed: rss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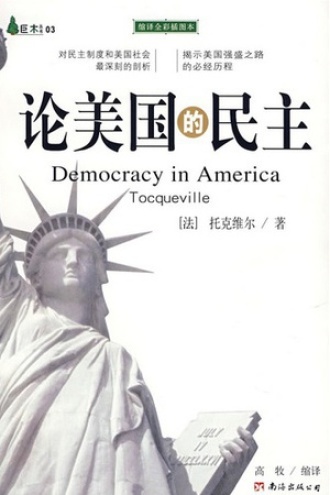












0 有用 夏珞 2008-06-09 16:44:24
装帧不好。
1 有用 风向未来吹去 2012-07-04 07:17:00
任何一种环境或一个人,初次见面就预感到离别的隐痛时,你必定爱上他了。
6 有用 眠去 2012-08-06 09:46:56
学苑书店你居然连这本书都没有,你真的要完蛋了
0 有用 艾習角™ 2014-06-27 15:06:54
小学留级三次的黄永玉,艺术上一直有趣有心有种。更喜欢意大利部分,尤其是写人部分,比如那个钟表匠和高龄的意大利兄弟。
0 有用 宛在水中央 2012-04-17 23:35:24
很可爱的插图呀。还没有去过翡冷翠(佛罗伦萨),还有很多远方没有走到。
0 有用 山新竹 2024-10-14 23:09:56 北京
可爱可爱太可爱了,怀疑这世上有人是神仙下凡,黄永玉就是。翻开画册,从巴黎开始,想到和哥哥在塞纳河边跑步的时光啊,好浪漫,没见过才华馥比仙的大神,可是神仙的日子我也有过。
0 有用 Elsa 2024-03-11 20:02:46 海南
补记
0 有用 赖赖懒懒 2023-12-22 23:57:03 法国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世说新语》,这是黄老先生的人生座右铭。 几经风雨,不愿妥协。
0 有用 方一 2023-06-24 09:59:25 浙江
老爷子的文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写到一些文革的边边角角,浮光掠影间可以瞥见历史角落里的残酷。一代人就这么过去了,怅然若失。
0 有用 冰冻呼吸 2023-06-14 19:39:25 上海
真正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