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儿借这本书 · · · · · ·
以下书单推荐 · · · · · · ( 全部 )
- 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由于非技术原因,仅显示99种) (迎风追)
- 20世纪100部最佳中文小说 (bookbug)
- 别样中国史 (jiaon)
- 20世纪中文经典小说200部 (东方快车)
- 世纪文学60家 (东方快车)
谁读这本书? · · · · · ·
二手市场
· · · · · ·
订阅关于狗日的粮食的评论:
feed: rss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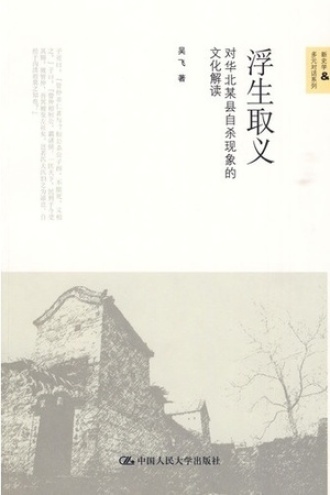













1 有用 酒徒 2012-03-29 00:03:28
农民不能吃饱太作孽
5 有用 ✖ 2009-01-03 00:19:53
这没滋味儿的话说了足有三十年。它显不出味道是因为那天早晨以后的日子味道太浓的缘故。"够日的粮食!",哪里是骂,分明是疼呢。是不是骂,骂个谁,得问在她坟上蹓跶的天宽,老家伙心里或许明白。
0 有用 乱 2007-11-15 18:41:47
狗日的~~~~~~ 粮食。。。。。。。。。。。。。。
1 有用 kiiro 2011-06-04 18:17:31
大都用男性的软弱衬托女性的人格魅力,每个男主人公都让人浑身不舒服却又感觉这才是现实
0 有用 要啥自行车 2012-09-12 00:23:04
在厕所里读完了它。为了让家里能多吃口,得罪了所有的人,包括自己男人。熊男人你真他妈怂。
0 有用 起舞 2024-07-21 11:12:46 安徽
瘿袋曹杏花为这个家操持到死……坚韧顽强不因外貌而自卑的女性形象。看到结尾处,不禁感慨、养儿养女有什么用
0 有用 我城 2024-07-02 22:18:55 广东
很饿啊,想要满足食欲,想要满足爱欲,想要活下去,于是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欲望,于是有了曹杏花。活着的瘿袋是千千万为“狗日的粮食”费尽脑汁和心思、以让全家人活下去为荣的婆娘们,但死了的时候她只是那个两百斤粮食背来的女人。 和其他新写实小说家不太一样,它这个真的很有一种痞气和某种喧嚣,挺喜欢的。
0 有用 藤花瓜瓜 2024-04-21 21:24:16 江苏
可恨的不是粮食
0 有用 🌙 2024-04-09 08:08:50 江苏
“那些不加修饰的逼真叙事,带着生活原生态的躁动和热烈,使那些粗鄙的日常现实变得生机勃勃”
0 有用 莺粟沉入水中梯 2024-02-14 04:29:17 江苏
食色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