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 · · · ·
1772年初夏的一个早晨,伦敦城内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威斯敏斯特厅,静静等待王座法院大法官做出一个决定人类未来的判决:黑人奴隶是否应该获得自由?判决的消息犹如一阵旋风刮过大洋,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无数黑人间点燃了一场希望之火。他们挣脱奴役的锁链,从此奋身于追求自由的斗争中。
在本书中,西蒙·沙玛以激情澎湃、超群绝伦的叙事艺术,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众多不知名的废奴主义者与黑人为解放奴隶而斗争的故事。他们认为,自由是属于全人类的权利,不因肤色有别。废奴者们在法庭上为遭人绑架的黑人慷慨陈词,带领他们穿越枪林弹雨的北美战场,横渡风暴肆虐的大西洋,最终重返非洲故乡,在野蛮荒芜的塞拉利昂开创新的国度。蓄奴者的阻挠、革命者的虚伪、英国政府的干扰,甚至黑人同胞见利忘义的背叛行径,种种艰难险阻,都无法泯灭他们追求和捍卫自由的决心与勇气。
风雨横渡的创作者
· · · · · ·
作者简介 · · · · · ·
西蒙·沙玛(Simon Schama),英国作家、历史学家,曾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及艺术史教授,在艺术史、荷兰史和法国史方面尤有建树。著有《爱国者和解放者》《风景与记忆》《伦勃朗的眼睛》《犹太人的故事》等,作品曾荣获沃尔夫森奖、W. H. 史密斯文学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沙玛还在BBC电视系列纪录片《英国史》《艺术的力量》《文明》中担任撰稿人和主持。
目录 · · · · · ·
主要人物
“英国·自由”的希望
第一部分 格里尼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二部分 约翰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结束,开始
大事年表
注释与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致谢
索引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 · · · · ·
-
詹姆斯·曼斯菲尔德发表了可能是整场诉讼中最夸张、最张扬的辩词。詹姆斯·曼斯菲尔德假装自己是詹姆斯·萨默塞特,说道:“确实,我曾经是一名奴隶,在非洲被役为奴。铁链加身,我被送上一艘英国的船,从非洲去了美洲……从人生的第一刻到现在,我从没有在一个我能维护自身基本人权的国家生活过。现在,我终于来到一个以尊重法律、保障自由而闻名的国家,你们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不受这些法律保护,而是要再一次被送走、卖掉吗?”谁都说不出来。黑皮肤的萨默塞特也是人,不是吗?那么,除非是英国背着国家宪法出台了什么新的财产法,否则他在英国便永远不可能是奴隶。——《风雨横渡》第二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丛书信息
· · · · · ·
喜欢读"风雨横渡"的人也喜欢的电子书 · · · · · ·
喜欢读"风雨横渡"的人也喜欢 · · · · · ·
风雨横渡的书评 · · · · · · ( 全部 10 条 )
不列颠·弗里德曼,从莱克星顿到塞拉利昂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在开始时候就很有意思的一本书。西蒙·沙玛先讲了十三个殖民地方面和伦敦本部就茶叶税的撕扯不清,然后漫不经心地插播了一句,有气急了的英国方面在殖民地的驻军领袖说,如果殖民地再不知好歹,就煽动黑人奴隶暴动革命,借此给殖民地人一点颜色看看。哪知道这种风声传了出去,... (展开)黑人奴隶与白人摩西:一段尘封的历史
> 更多书评 10篇
当前版本有售 · · · · · ·
这本书的其他版本 · · · · · · ( 全部6 )
-
Ecco (2006)暂无评分 1人读过
-
Harper Perennial (2007)暂无评分 1人读过
-
Oberon Books (2008)暂无评分
-
HarperAudio (2006)暂无评分
以下书单推荐 · · · · · · ( 全部 )
- 理想国译丛 [MIRROR] 完整书单 (理想国)
- 鎮長的新書列 (鎮長)
- 理想国译丛[MIRROR](已出版书目) (Yursler_钰)
- 豆瓣读书非虚构首页推荐自选 (天雨流芳)
- kindle 2 (甜賽)
谁读这本书? · · · · · ·
二手市场
· · · · · ·
订阅关于风雨横渡的评论:
feed: rss 2.0



![[英国] 西蒙·沙玛](https://img3.doubanio.com/view/personage/m/public/e554ee0847bb7ec7ad1f18a01a9ae7e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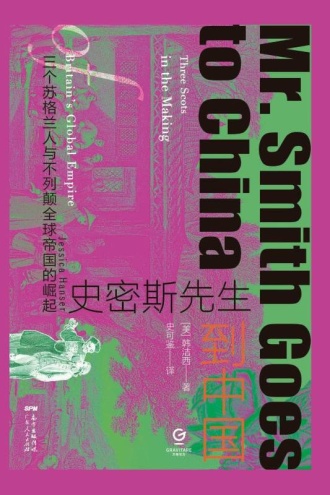
















1 有用 深山夜读 2021-10-31 14:48:56
可与《自由的流亡者》一起读,《自由的流亡者》是说美国革命中忠于英王的那批人后来如何了,这本说那批人中的黑人后来如何了……还是第一次详细了解了塞拉利昂的那段历史
4 有用 别格莫特 2021-02-27 23:10:35
断断续续看了俩礼拜,第一本译丛没有劝退,妥妥的知识盲区啊。配图里那张运奴隶的船图还是很震撼的。
1 有用 绍牧 2021-03-21 04:11:19
挺好读的,不知道算不算历史非虚构,史料怎么找的呢?又集中又少见,算新视角吗?
5 有用 东海舟龙马 2021-02-24 15:49:44
英国空气太纯洁了,不适合奴隶呼吸。没有什么比自由更为珍贵!
3 有用 与影牵手 2021-02-18 08:49:56
★★★黑奴回归这个题材很有趣,可是书不精彩。
0 有用 墨氅随风翩 2024-05-16 10:28:22 河南
原来早在福音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英国就已经将废奴这一议题正式摆在桌面上讨论,甚至早在都铎王朝时期就留下了名言“英格兰的空气不适合奴隶呼吸”。一般认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出发点在于收税和议会席位的争议,沙玛整理信息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先是威斯敏斯特废奴呼声的日益高涨本就令北美十三州白人地主们不满,而独立战争爆发后大不列颠军事力量的不足迫使总督们接连打出废奴牌,废奴牌又反过来迫使大批中立的白人地主加入华盛... 原来早在福音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英国就已经将废奴这一议题正式摆在桌面上讨论,甚至早在都铎王朝时期就留下了名言“英格兰的空气不适合奴隶呼吸”。一般认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出发点在于收税和议会席位的争议,沙玛整理信息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先是威斯敏斯特废奴呼声的日益高涨本就令北美十三州白人地主们不满,而独立战争爆发后大不列颠军事力量的不足迫使总督们接连打出废奴牌,废奴牌又反过来迫使大批中立的白人地主加入华盛顿,最终使北美十三州的力量彻底失衡。而无论怎么讲,英国贵族们的修养也让他们选择兑现曾经的承诺,哪怕仅是面子上的,于是黑人领地从纸上成为现实,也就是书名风雨横渡,跨过大西洋在塞拉利昂建立定居点。但仔细看下来,这段历史还是很草台班子的,说白了不管是废奴主义者还是黑人,对未来都没什么纲领。 (展开)
0 有用 陌上~羽 2024-05-12 21:09:13 海南
叙事平淡,如看历史书
0 有用 熊羊 2024-02-23 22:26:12 海南
1. 早几年因为写论文而想要读的书,拖到如今才终于看了。发现原来和我当时的论文主题简直没有什么关系。2. 对于一个英国人写英国如何解放美国奴隶这件事情,我内心还是有一些狭隘的怀疑。但是整体上从科普一段历史,提供一个看待奴隶解放发展的新观点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此书还是相当不错。约翰克拉克森带领黑人移民横跨大洋,重返非洲的部分看的我简直抓心挠肝,热血沸腾。果然燃还是真正充满抗战和开拓的历史更燃。3. 虽... 1. 早几年因为写论文而想要读的书,拖到如今才终于看了。发现原来和我当时的论文主题简直没有什么关系。2. 对于一个英国人写英国如何解放美国奴隶这件事情,我内心还是有一些狭隘的怀疑。但是整体上从科普一段历史,提供一个看待奴隶解放发展的新观点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此书还是相当不错。约翰克拉克森带领黑人移民横跨大洋,重返非洲的部分看的我简直抓心挠肝,热血沸腾。果然燃还是真正充满抗战和开拓的历史更燃。3. 虽然忘记人名,但是只要分清人物的立场——黑人白人等就可以逻辑通顺地推进阅读。 (展开)
0 有用 卷心菜王 2024-01-21 22:25:18 北京
美洲支持保皇党(英帝国)的黑人奴隶在英国国家个人公司支持下返回非洲大陆定居的历史故事,弥补了知识盲区,不过写得不够吸引人。
0 有用 蜜柑蜜柑蜜柑 2024-01-09 09:03:42 重庆
原来风雨重渡是这个意思,是从加拿大重渡回到西非去建立塞拉利昂,这个在乾隆年间的短暂的共和制,果然大历史里面中小故事精彩绝伦